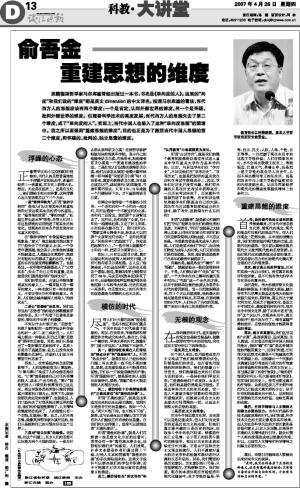|
 |
|
|
2007年4月26日 |
|
||
| 俞吾金 重建思想的维度 本报记者 林丹 整理 周广利 摄 |
| 美籍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是《单向度的人》。这里的“向度”和我们说的“维度”都是英文dimension的中文译名。按照马尔库塞的看法,当代西方人的思想应该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肯定、认同外部世界的维度,另一个是怀疑、批判外部世界的维度。但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当代西方人的思想失去了第二个维度,成了“单向度的人”。实际上,当代中国人也陷入了这种“单向度思想”的困境中。我之所以要强调“重建思想的维度”,目的也正是为了激活当代中国人思想的第二个维度,即怀疑的、批判的、独立思索的维度。 浮躁的心态 正像贾平凹的小说《浮躁》所描绘的,当代人的思想普遍地处于浮躁不安的状态中,希望在经济上一夜暴富,在文化上获得大名。然而,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他们都缺乏相应的积累。这种浮躁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修辞学转向”。所谓“修辞学转向”是指人们从对现实生活的重视转向对表达现实生活的语句的重视。如“超常规的发展”、“零的突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等等。尽管人们用上面这些漂亮的话语描述了现实生活的变化,但现实生活本身并没有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 在“修辞学转向”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意义”概念被滥用到以致于它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比如,一个学者申请课题,他会表示,如果他的课题不能被通过,人类就会在黑暗中。既然所有轻的东西都成了重的东西,于是,重的东西也就变得轻飘飘的了。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和课题都进入了“太空状态”,失去了自己应有的重量,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批评的“泡沫文化”。 我们的看法是,应该让事物恢复到原初的意义上。一棵草就只有一棵草的意义,一杯水就只有一杯水的意义,不要去夸大任何事物的意义。否则,人们就会越来越深入地陷入“泡沫状态”。 二是让“思想者”去思考。我们这里说的“思想者”指的是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即一个托着下巴苦苦思索着的、裸体的中年男子的塑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思想者”的照片被粘贴在一些哲学社会科学杂志的封一、封二、封三或封四上。人们竭力摆出一种姿态,即自己正像“思想者”那样在思索着。其实,他们只是做出了一副好像在思索的样子,实质上却是为了逃避思索。总之,让没有生命的雕像去思索吧,活着的人们却不再需要任何思索了。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影响下,人的理性蜕变为计算理性,“计算与算计”构成了人的全部思维活动。“计算”就是检查自己对任何事情的投入、成本、产出与利益,“算计”就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算到自己这边来。商店里服务员的笑容只维持到钱离开顾客的口袋为止,再笑下去,就是脸部肌肉运动的浪费了。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空灵的庄禅世界的留恋,他们的价值理性萎缩了,人文精神的维度闭合起来了,人的理性只有一个功能,即就是计算。总之,人们不再思维,就像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的,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三是对“诺贝尔奖”的怨恨。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至少人们的思想可以体现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为什么那么崇拜诺贝尔奖?法国哲学家萨特就写信给瑞典科学院,表示自己拒绝接受诺贝尔奖。在他看来,拒绝接受诺贝尔奖是一个更富有挑战性的举动。二是即使人们试图去获得诺贝尔奖,他们应该怎么做呢?是整天像祥林嫂一样叫喊着“我要诺贝尔奖”吗?在我看来,真要去获得诺贝尔奖,首先就应该忘记它,退回到自己的实验室、书房和图书馆去。只有5年、10年地就一个问题钻研下去,才可望获得诺贝尔奖。 在禅宗中流传着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一起过河,在河边遇到一个不敢过河的女孩。老和尚二话没说,就把那个女孩背过去了。过河后,老和尚放下女孩,与小和尚一起继续赶路。又走了好几里路,小和尚实在憋不住了,责问老和尚:“儒家说男女授受不亲,你怎么可以把那个女孩背过河去呢?”老和尚笑着说:“其实我早已把她放下了,你却还把她背在心上。”一些中国人就像那个小和尚一样,把诺贝尔奖背在心上。 实际上,只有忘记诺贝尔奖,真正以超功利的态度深入地研究问题,才有可能与诺贝尔奖相遇。古人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据说,歌德写《浮士德》前后花了60年,马克思写《资本论》则花了40年,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则是他沉默12年的伟大结晶。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在思想文化上的任何伟大的创造都是与浮躁的心态无关的。 模仿的时代 尽管人们天天都在高喊“理论创新”,但却不能证明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时代是富于创意的。相反,在我看来,平庸琐碎和矫揉造作才构成它的本色。换言之,它是一个模仿的、平淡无奇的时代。就像所罗门国王所说的:“太阳底下无新事。” 其一,模仿特征表现在人们常说的“热点分析”和“跟踪研究”上。所谓“热点分析”,就是在别人已经炒热的问题上再去发表一些不伦不类的意见。显然,这些意见根本不可能具有独创性,它们从一开始就是模仿的产物;所谓“跟踪研究”,就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做研究。显然,“跟踪”是不可能走到别人的前面去的。 其二,模仿特征十分典型地表现在“正确的废话”和“隐性的抄袭”上。 所谓“正确的废话”,就是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话永远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是没有任何信息量的。假如一个人说:“明天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雨”,显然,这句话是永远正确的,但它并没有向人们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量。在我们的大众传媒上,经常可以读到这类“正确的废话”; 所谓“隐性的抄袭”,就是人们在解读一些思想文化方面的论著时,常常会有一种“落花流水春去也,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人们发现,许多文本都是作者们通过网上下载、对他人文本的剪辑等“隐性的抄袭”的手法拼贴起来的。这类文字或许可以解决他们的学位和职称,却不可能真正对学术做出富有实质性意义的推进。 其三,模仿特征在“应试导向”和“认同教育”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所谓“应试导向”,就是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都是以通过考试进入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作为基本导向的。比如,与其说学生们在“学历史”,不如说他们在“学考历史”。“学考历史”,也就是把钻研的重点放在如何在考试中获得高分上,因此,学生们对历史并没有兴趣,他们有兴趣的只是在历史考试中获得高分。一旦历史考试结束了,历史教科书就被扔进了垃圾筒,历史知识也很快地被学生们驱逐出自己的大脑。因为在与应试教育制度相适应的大脑中,除了考分,还能储存什么东西呢? 所谓“认同教育”,就是家长和教师们把“听话”理解为学生们的最优秀的品质。无庸讳言,“听话”也就是让大脑停止思索,让学生们对家长和老师们的任何见解取简单认同的态度。不可思议的是,当受教育者还是未成年人的时候,人们总是要求他们“听话”,而当他们转变为成年人的时候,人们又要求他们具有创造性。其实,他们的创造性早已在早年的教育中被扼杀了。 有趣的是,越是热衷于“模仿” 和“跟踪”,就越要装出一副独创性的样子。于是,人们便诉诸于“化妆”或“包装”。一个大学生在自己撰写的履历表中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出色的才俊,以至于招聘单位竟把他误认为是青年时代的爱因斯坦。但一旦把他招聘进来,在3个月以后就发现,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即平庸。在崇尚模仿的时代中,人们失去了内在的灵魂,剩下来的只是自己的美丽的外表。 无根的观念 在崇尚模仿的时代,甚至连流行的观念也是缺乏根基的,就像漂浮在空气中的肥皂泡。我在这里主要分析以下两种观念: 一是实用主义观念。 对个别人来说,实用理性或实用主义构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便是他们的信念,也打着实用理性的深深的烙印。他们的想像力十分贫乏,他们能够提出来的只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保佑他们平安无事;二是确保他们升官发财。由此可见,信仰的基础仍然是实用理性。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生活态度,使一些人不愿意去维护抽象的法律原则和道德原则,而极易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周围的一切,从而达不到相应的思想的高度。 二是历史主义的观念。 在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历史剧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但人们对历史采取的却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即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历史的泡沫,如政治斗争中的机巧权谋、矫揉造作的儿女私情、公子哥儿的好勇斗狠和宫帷秘事。相反对历史的本质却缺乏任何兴趣。正是由于这种历史主义观念的流行,人们不愿意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历史意识。历史意识的口号是:只有理解现在,才能解释过去。我们知道,现在的本质体现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中,其主导性价值是:平等、自由、民主、人权、人格、个性、公正等等。一旦把握了现在生活中的这些主导性价值,人们在探索历史时,才不会再去歌颂王权至上、等级观念、江湖义气、男尊女卑,而是把上述主导性的观念导入历史中,从而不再去撰写帝王的私生活,而是把历史中与上述主导性价值相切合的内容发掘出来,从而为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提供精神上的亲和力。 重建思想的维度 首先,坚持现代性的立场和后现代性的眼光。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前现代的观念、现代的观念和后现代的观念并存,使人们在观念上茫然失措。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们仍然要坚持现代性的立场,走现代化的道路,但又要认真地借鉴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从而对现代化的道路做出必要的修正,使其沿着比西方的初始现代化模式更合理的方式向前发展。 其次,确立真正的批评意识。历史和实践一再启示我们,没有真正的批评和批评家,是不可能有伟大的学术文化事业的复兴的。 众所周知,伟大的俄罗斯文化就是被别林斯基、杜勃留波夫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伟大的批评家提升起来的。同样地,葛兰西之于意大利文化、尼采之于德国文化、鲁迅之于中国文化,都起着同样的作用。但在当今中国文化界,除了词典中还有“批评”这个词以外,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批评已经不再存在了。唯有重建严肃的批评,思想的独创性才能获得普遍的尊重。 再次,确立求真意识。我们这里说的“求真”,是指讲真话、追求真理、为人真诚。正如鲁迅在批评中国人的国民性时,强调“瞒”和“骗”是这种国民性的消极因素之一,而我们知道,任何伟大的思想文化都是不可能建筑在谎言和欺骗上的。而能够对一个民族的求真意识进行考查的乃是它的忏悔意识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在西方历史上,有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卢梭的《忏悔录》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但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忏悔录。众多回忆录几乎无例外地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少女,似乎所有的罪恶都来自于别人。这样的回忆录既缺乏历史的价值,也缺乏真诚的态度。 最后,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当今时代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我们知道,科学技术关注的主要对象是事实和效率,而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主要对象则是价值和意义。比如人体克隆,如果没有正确的人文精神进行引导,就会对整个人类的发展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所以,应该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
最后,我想引用德国诗人歌德的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 “是的,我完全的委身于生活的这种意义,这是智慧的最后结论:只有每日每时去开拓自由和生活,才会有生活和自由的享受。” |
|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