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湖北英山县,30年后重读《凤凰琴》
刘醒龙:以文学改善人心
本报记者 张瑾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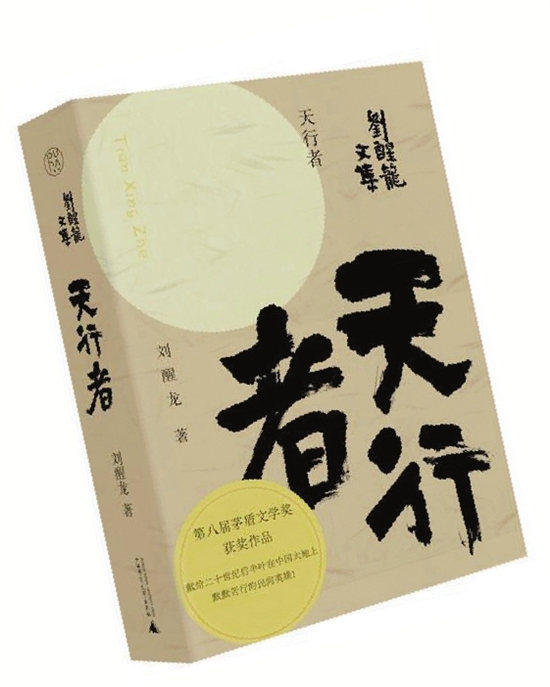 |
到湖北英山县,30年后重读《凤凰琴》
刘醒龙:以文学改善人心
这个夏天,我从杭州出发,经4个半小时高铁到武汉,再从武汉坐车上高速,2个小时后到达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重读20世纪90年代初横空出世的《凤凰琴》,同时寻访一位春风悦读榜的老朋友刘醒龙的过往与当下。
说到他与钱江晚报浙江新华主办的春风悦读榜的关系,很多读者都知道,他担任过这一文学盛事的评委,还作为演讲嘉宾在2021年1月1日的书香迎新跨年活动中,细说“坐对西湖三十年”。
作家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发表于1992年《青年文学》第五期。2009年,从中篇小说《凤凰琴》最后一个字开始续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首次出版,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抵达的那个晚上,在英山县大礼堂,我看到了老电影《凤凰琴》。英山县是一座山里的小小县城,也是刘醒龙的故乡。
刘醒龙30年前就关注到了大别山里一群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的身份,是民办教师。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刘醒龙延续了对乡村小学的关注,而教育常新,困境依然存在。
文学的意外之喜
可遇不可求
钱江晚报:如今回头看《凤凰琴》,您有一种怎样的感觉?如果现在让您重写,您会有新的想法吗?
刘醒龙:这几年因为再版过程中的技术性原因时常校阅旧作,对《凤凰琴》不仅从没有过遗憾,还时常从中获得某些启示,就像与一位至情至性的老朋友重逢。文学中的爱情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爱情是万万不能的。《凤凰琴》中的爱情是一种苦恋,一部中篇小说难得同时兼顾一群乡村教师的困局,到了《天行者》,有了篇幅长度的保障,爱情得以舒展地写开。
钱江晚报:在英山县的这几个晚上,我都在读《天行者》,今天读来依然是很震撼的。在其中看到了乡土中国的一面,看到了更丰富的情感,更多的张英才们,他们来过,又走了,万物生长,界岭小学也如是。您怎么看待作家的“城市写作”和“乡村写作”,您仍然把自己归为中国“乡村写作”的代表人物吗?
刘醒龙:怎么看是别人的事,怎么归类也是别人的事,怎么写才是自己的事。那些了不起的“乡村写作”往往会将城市看得很透彻,只有将城市看清楚明白后,才有可能作为乡村的镜子,使得二者既有融合,又有区分,这时候的乡村写作才会是有效的,长久的,否则很难越过概念化这一关。
钱江晚报:《凤凰琴》前后,你对文学影响社会的功能是怎样看的?你曾想过《凤凰琴》可以改变那么多现实中的乡村教师的命运吗?这是否超出了文学的预期?30年后,文学的功能是否依然可以这么强大?
刘醒龙:文学对社会生活的改变,并非是文学必备的功能。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主要通过对人心的改善。
看上去《凤凰琴》直接改变了乡村教师的命运,实际上首先是它对主导乡村教育事业的那些人的心灵的影响。从这一点上看,文学的社会功能依然存在,之所以见不到,是由于心太急,将文学作品当成政策法规。文学只能是文学,甚至只能是百分之百的文学,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当然,也不能排斥经典文学超出文学范围,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的效果只能是意外之喜,可遇而不可求。
敬重心向乡村的人
也理解离开的人
钱江晚报:您对现在的支教者怎么看?可能他们在出发前的理想是一回事,到了山区、边地,有些支教者发现“现实很骨感”,对自己当初的理想产生了怀疑。新时代的支教者,跟您笔下的张英才、蓝飞、夏雪等乡村教师一样,来了,又走了,时间长短不一,您对这个群体有所了解吗?
刘醒龙:因为骨感的现实,才体现出理想的光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去长江三峡采风,遇上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教师,他进师范学校的第一天读的是《凤凰琴》,离开校园的前夜依然读的是《凤凰琴》。后来我专程去那所小学校找他,学校的老师指着身后更高的大山说,他去山上的另一所学校了。当时心里非常难过,觉得是自己害了人家,如此阳光的一位大男孩,今后会有怎样的生活等着他呢?还是小说中的那些人说的那些话,我敬重一切有心向着乡村的人,也理解一切离开乡村的人。
钱江晚报:中国历史大进程中,一些名词,一些事物消失了,比如民办教师,比如粮票等,我们现在回看,《天行者》中描述的重要时代背景,是真的消失了吗?我们又发生了疑问,我们现在是在回味消失的事物吗?
刘醒龙:没有记忆就没有人生,记忆是人生的重要组成。所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种背叛,是对人生而言。一个人明明来自乡村,却对乡村咬牙切齿,甚至还有其他一些让人不堪的举动,好比硬生生地将人生的一大块切割掉。这样残缺掉的人生,如何能让整个人好起来?任何对过往的回望,本质上都是对只有一次的生命负全责。
钱江晚报:这个年代,旧事物迅速退去,新事物大浪拍岸,作家怎么看待新与旧的关系,会不会有种面对新事物无所适从而失去表达的欲望?
刘醒龙:在文学中,新与旧的关系,与一般情形不同。一部小说的诞生,从构思到写作,再到发表或出版,需要较长的周期。在时空中,文学与别的媒介的可比性,只存在于作品存世的时间长短,而不会在谁更及时上作比较。任何新事物,只要没有构建新体系,没有形成新经验,在文学中只会以非同寻常的细节的面貌出现,不可能巅覆现存的文学态势。作家最不缺的就是表达的欲望,也不会对新事物无所适从,因为作家一旦失去表达的欲望,又对新生活无所适从,就等于宣告一个人作为作家的生命终结了。这时候的作家,就等于百米赛跑,都过终点线了,还要继续向前跑一阵,那种百米线之外的跑动,是无效的,无意义的,不过是为了证明之前的参与。
没有哪位作家
能完全超越地域性
钱江晚报:您的生长之地湖北黄冈,以“惟楚有才,鄂东为最”著称,这几天,我们跟着您领略了黄冈之美,又与大别山不可分离。地方特色的书写对作家来说是必须的吗?有没有一位作家,可以完全超越地域性?
刘醒龙:越是地域性的越是全世界的,这话有人信,也有人不信。我是信的,起码我没有发现同行中谁做到了对地域性的完全超越。反而是发现那些口碑最好的作品,无一不是出自某个地域,并且不曾有过超越这种地域的企图。连最了不起的神都有局限性,何况那些凡夫俗子中的佼佼者。他们能写透黄河,到了长江边,就又成了迷茫者。认清自己的局限,反而能够成就内心的大格局。如果这样的格局,是对地域性的超越,那就是可以的。
钱江晚报:我们来到英山县,看到英山县当地也看中了《凤凰琴》三十周年带来的商机,想以此推动文旅,我记得四川作家阿来说过,他常常因为一部文学作品去某个地方打卡。您觉得,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是否能有这种能量?
刘醒龙:这种情况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一个作家能够带着自己的作品回到家乡,是无比地荣幸,阎晶明(注:中国作协副主席)在开幕式上说的这话,很有力量,也很有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