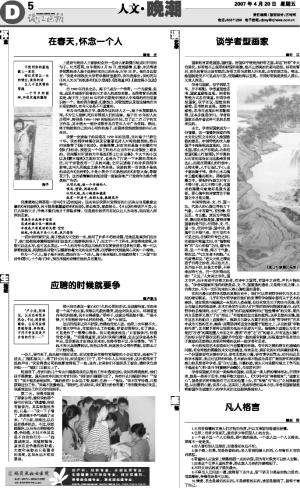画家的首要是画画,画好画。好画似乎便是指好看之画,却这“好看”中大有讲究。好看绝不止观看的舒服和刺激,绝不止漂亮的色彩与造型。好看的背后,形色的背后应该有想法,好看之看当发前人所未发,应有独到之处。唯此,绘画就是使不可见成为可见,使隐藏的得以呈现。所谓好看就是既悦人眼目,又发人深思。
学者与画家,似乎两轨之车,并不相配。学者重理性思考,画家重感性直观。两者的智性方式各有倾重。所谓学者型画家,似乎在说:理性型的感性,思考性的直观。理性与感性,思考与直观如何相配相得,这本身就是学问。学者型画家正是冲着这种可见的思想来说的。
由之,学者型画家成为一份憧憬,这一憧憬怀揣着向伟大文化记忆之中的文人绘画致敬的意思。中国传统的文人绘画并不纯是现成直观的。如山水画,那山水并非现成。北宋范宽画《溪山行旅图》,并非真的从对面的某处如此这般地看到这山,而是在那溪山的行旅中,山转水移,入于目而汇于心,出于意而凝于神,眼中山水与胸中丘壑相叠而相生。那绘画笔墨之中,那观听行游之时有万不得已者。此万不得已者,此画者的胸襟与意境却是最为重要。那心胸中的诗意贯注于绘画之中才是关键。
中国传统诗、文、书、画一体,代表人的心胸世界的万千气象。心中有豪气、有怡情、有远思、有丘壑,发而为声就是诗,聚而呈形就是画,兼得诗情画意的是书法。所谓诗、文、书、画一体,使诗中画、画中诗,那胸中万不得已者,在可见和不可见之间,在倾听和专注之间,在牵挂和相望之间,在“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之间,通行无碍,呈一个和境,得万千气象。荀况说:“气之至者不两能。”元代黄漕却说:“若夫天机之精而造乎自得之妙者,其应也无方,其用也不穷,如泉之有源,不择地而皆可出,岂一艺所得而名欤?”又说:“人知诗之非色,画之非声,而不知造乎自得之妙者,有诗中之画焉,有画中之诗焉,声色不能拘也。”学者型画家所指向的既是诗、文、书、画兼通的通者,又是得天机之精、入自得之妙、不为一艺所拘束的天地心胸相通的通者。
在西方漫长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研究与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大哲学家在他们的宏博哲学命题中都有关于艺术的牵涉。诸如现实与超越这一永恒的人类命题,往往化变为关于肉体与灵魂、现世与超世的两难选择,艺术正是使在世的人们可能在两岸间摆渡的船舟。近代哲学的思维倾向,由对“上帝天国”的归返渐渐转向对“理性精神”的关怀。现代西方思想界又展开了对“形而上”和理性优位立场的批判。众多思想的交锋,就在这艺术的船舟上直接展开。雅斯贝尔斯认为真正的艺术是“哲学研究”在其中成为可能的艺术。梅洛·庞蒂强调将直觉体验置于理性之上,从而扯破“事物的外表”,艺术赋予那种世俗眼光视而不见者为可见。海德格尔直接认为艺术是把“在者”的真理置入作品之中,澄明“在者”之“在”的意义。所有这些只鳞片爪的标示似乎都在说明:画家并非创造一般的感官刺激,而是通过作品来使关于真理的思想得以实现和传播的这样一批学者和思者。
今天的视觉艺术创造面对日益繁复的环境。有中西之辨的跨文化境域的问题,有全球性的图像技术文化的挑战,有商品化、娱乐化的时尚风潮的影响。一个好画家要有足够的学识,要有思想的力量,要有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学术胸怀,来应对这样的环境。艺术家如果不能成为具有广阔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思想者和学者,虽“日对丘壑,日摹妙迹,到头只与采髹圬墁之工争巧拙于毫厘也”(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与某匠何异?
学者型画家并非某一类特殊的画家,而是某一类人群的精神形态。所谓学者,就是一类善于思考、穷极事物之理的人。《大学》中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要求将事物放在它应在的位置上去,在“知物”与“知己”之间推极道理,从而澄明心意,供养心志。这实际上是成事者的基本方法。学者型画家就是将绘画作为诚意正心的学术来如此这般地推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