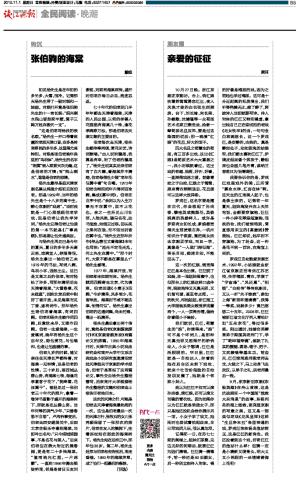张伯驹的海棠
戴维
初见杨先生是在年初的多伦多,大雪,很冷。记得那天杨先生带了一副对联和一轴画。对联打开竟是张伯驹先生的十一言长联:“绍兴剩水残山留赵家半壁,箕子三韩万姓存殷氏一支”。
“这是伯老写给我的嵌名联。”杨先生一开口带着浓重的老派天津口音,在多是岭南移民的多伦多,这显得尤其特别。对联是张伯老晚年典型的“鸟羽体”,杨先生的名字“绍箕”嵌入联首天衣无缝,这是伯老的才情;而“残山剩水”,隐隐是伯老的悲情。
杨先生最早是经天津京剧名票从鸿逵介绍初见张伯老。那是1959年,当年的杨先生是个十八岁的高中生,醉心京剧的“戏迷”。“当时我就是一门心思想跟伯老学戏,但是伯老让我先学诗词。”杨先生记得伯老让他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广事类赋》,那是要让他先通典故。
与杨先生再见已是今年的夏天,夏日的多伦多天高云淡,凉爽宜人,舒服得很。杨先生拿出一轴伯老乙未1979年的书法,写词八阙,鸟羽小字,迥然出尘。这已是文革之后的伯老,相对轻松了许多,写那年清明后去天津看海棠,“大雪春寒,花未做蕊”,回到北京后家中刚好丁香开放,未见海棠而见丁香,遂有词作。那年杨先生陪伯老看海棠,有词四阙。伯老和杨先生韵作词四阙,后意犹未尽,又续作四阙。伯老一生爱海棠,一生爱填词,晚年有杨先生这个忘年交,陪他赏花,与他唱和,也是让他温暖的事。
伯老九岁的时候,随父亲住在天津长芦都转署,对海棠一见钟情,这是伯老的性情。三十岁后,居西城丛碧山房,有海棠七株,每逢花季宴客于花下,“拥绛雪、花压阑干”。曾经见过一张伯老三十年代的照片,拿着一卷诗书留影于盛开的海棠树下,那就是在丛碧山房。当年何等的英气少年,“只替春愁不自愁”。卢沟桥事变后,伯老去西安避居关中,后回北京在极乐寺看到海棠,当即吟出名句:“只今倾城倾国事,不是名花与美人。”后来伯老住在燕大附近的展春园,更是有二十多株海棠。“值雨流光红湿,一片迷蒙”。一直到1956年搬去银锭桥南,邻居是昔日旧友刘紫铭,刘家有海棠两株,盛开时伯老亦每日必去,流连忘返。
七十年代的伯老则几乎年年都去天津看海棠,天津的人民公园,以前的李善人花园里有海棠几十株,逢花季娉婷万态。那是伯老去天津文聚的主要目的。
伯老每次去天津,杨先生都侍奉两侧,赏花论艺,诗词酬唱。“古人说附骥尾,我算是有幸,附了伯老的骥尾了。”杨先生说其实后来伯老有了白内障,看海棠并不清楚,伯老每借杜少陵“老年花似雾中看”句自嘲。1973年伯老也特别把年内得词百余阙,集成《雾中词》。伯老在自序中说:“余则以为人生万事无不在雾中,故不止花也。余之一生所见山川壮丽,人物风流,骏马名花,法书宝绘,如烟云过眼,回头视之果何在哉,而不知当时皆在雾中也。”杨先生在那年所作《侍丛碧世丈看海棠》末句也写到:“池光不定花光乱,何止先生在雾中。”“那个时代,大家不都是在雾里么?”杨先生感喟。
1977年,海棠开放,而伯老却未如期而来。杨先生赋词四阙寄去北京,代为请柬。伯老回赠《小秦王》四阙,“今岁晴旱,风多雨少,花皆早放。海棠时节或不能去津,怅惘何似”。杨先生拿出伯老的这通词稿,尚未托裱,嗅出一纸清芬。
杨先生最后拿出两个信封,竟然是伯老《京剧源流探讨》和《京剧音韵身段》两篇论文的原稿。1980年海棠开时,天津市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会和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戏曲小说研究室邀请伯老赴天津做关于京剧的学术报告,伯老于是草拟了这两篇论文,事先交由杨先生整理誊写,后来南开大学根据杨先生整理的文稿和伯老会上报告印有油印本。
这次的天津之行,可能是伯老去天津看海棠最热闹的一次。这也是伯老最后一次的天津之行,张牧石的女儿张秀颖保留了一张那次的照片,伯老在友人的簇拥下,拄着拐杖站在怒放的海棠树下。杨先生站在后排正中,那年他38岁。第二年,杨先生赴京与伯老匆匆告别后,南走香港。1980年的海棠芳草,成了他们一起最后的春游。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