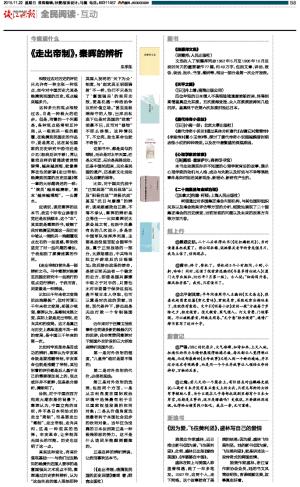《走出帝制》,秦晖的辨析
朱学东
相较过去对历史的评说只允许有一种主张一种观点,如今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晚清到民国的历史,观点越来越多元。
这种多元的观点相较过去,自是一种极大的进步。但是,附着的一个问题是,各种观点经常相互冲突,从一极到另一极的颠覆,在晚清到民国史的作品中,更是常见,这在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中恐怕还是少见(恕我见识不够),常让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迷惘错愕,越来越迷糊,就像秦晖在他的新著《走出帝制: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第一章的大标题表述的一样:“‘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一头雾水。
应该说,读完秦晖的这本书,我这个非专业读者自觉还是收获颇丰,这个“丰”,其实就是秦晖的书,破解了我对晚清至民国这一段历史中被从一端到另一端颠覆观点左右的一些困惑,帮助我坚定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于我起到了廓清迷雾的作用。
《走出帝制》首先是一部辨析之书。书中秦晖对晚清至民国史研究中一些流行的观点进行辨析。于我而言,则更像是一种辨误。
比如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说法流播甚广,但对何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却甚少梳理,秦晖认为,是秦制末路之变,实际上就是走出帝制,走向共和的变局。这才是真正与历史上鼎革逐鹿不再一样的变局,是中国三千年来的第一次。
比如对辛亥革命是否成功的辨析,秦晖认为辛亥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也就是推翻了帝制,其他附着的评价都是后人基于自己的需要硬加其上的,观点或许并不新鲜,但是条分缕析,清晰明了。
当然,对于中国在西方宪政大潮东渐的背景下,秦晖认为,中国立宪的目标,并不是日本明治式的走出“周制”,而是要走出“秦制”,走出帝制,走向共和,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辛亥革命,让帝制再无回头的可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这种变化,有其价值观基础——与我们过去熟知的晚清先进国人要学的是富国强兵之术观点不同,秦晖通过历史资料辨析,认为“这些先进的国人眼热那种英国人发明的‘天下为公’制度,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一样,他们不只是为了‘富国强兵’的实用功效,更是机遇一种政治争议的价值立场。”甚至连极端保守的人物,出洋后私底下也是对英国的“政教”倾慕不已,反而对“器物”不那么恭维。这种情况下,不立宪,发生革命也就不奇怪了。
这部书中,都是类似的辩驳,无论是对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无论是保路运动,还是中国站起来,无论是民国的遗产,还是新文化运动以及启蒙的思考。
比如,对于国共抗战中“正面战场”“敌后战场”以及“积极抗战”“消极抗战”甚至“抗日与摩擦”的辨析,读来颇感政治正确,不得不承认,秦晖的辨析是立得住——比如秦晖说太原会战之前,包括中共最有名的几次战斗,多是在中国军队指挥序列里,主要是战役层面配合国军作战,属于正面战场的一部分,太原陷落后,中共转向独立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游击战场的使命,是使日军无法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即便是国共摩擦中取之于对手的,只要他比对手更善于保持这些地盘不被日本人夺取,也可以算是对抗战的贡献,当然,现代条件下,游击战是无法打败一个专制强国的。
近年来对于汪精卫投敌事件也有诸多新的躲躲闪闪的说辞,我非常赞同秦晖对于弱国外交阶段的三大标准来辨析民国外交:
第一是对外依附的程度,“儿皇帝”绝对是要不得的;
第二是对外依附的代价,必须有底线;
第三是对外依附的选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功利角度在国际政治环境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国家权益发展的依附对象;二是从价值角度选择最有利于本国社会进步的依附对象。当年汪伪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一种极端邪恶的势力。这不是什么诡词所能颠倒翻案的。
正是这样的辨析辨误,让我很喜欢这本书。
(《走出帝制: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秦晖 著;群言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