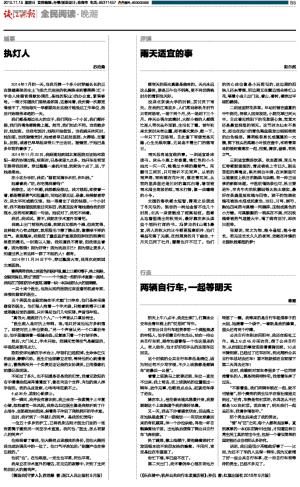执灯人
苏沧桑
2014年7月的一天,当我花费一个多小时穿越长长的正在修建高架的尘土飞扬坑坑洼洼的秋涛路来到曹燕燕(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她的职业)的办公室,累得够呛。一聊才知道我们居然是邻居,这意味着,我折腾一次都觉得受不了,而她每天一早都要如此这般才能抵达工作单位,然后开始艰苦卓绝的一天。
我们都是海边长大的女子,我们同住一个小区,我们都纤弱,我们的嘴角都微微上翘。然而,我们如此不同。当我散步时,她加班。当我吃饭时,她刚开始做饭。当我娱乐休闲时,她加班,当我睡懒觉时,她或者早已赶赴医院、火葬场、交警队、法院,或者已早早起来带儿子出去玩。睡懒觉,于她已是多年前的奢侈了。
2014年11月23日,我跟随她到城北某医院见证她和欧阳一家的协调过程,结束时,已是夜里九点多。她开车在前面引路带我回家。穿过整整一座杭州城,到家快十点了,这,于她是常态。
在小区分手时,我说:“器官采摘手术时,你叫我。”
她看看我:“说,你吃得消看吗?”
我惊住。这个问题,我想都没想过。我才想起,即使看一看,都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而她还要见证、录像、给捐献者穿衣、送太平间或殡仪馆。她一眼看出了我的怯弱,一个小时前,我不敢触碰医院里任何东西,我甚至没有喝她递给我的那瓶水,没有和家属说一句话。她说对了,我吃不消看。
我说,我试试。要不,我就在手术室外面看吧。
我晚上出门前刚洗过澡,到家后又想洗个澡,但我觉得,这样做内心有点愧疚,就用湿毛巾擦了擦头发,像擦掉不祥的空气。夜里醒来,我想起了重症监护室里欧阳肿胀的眼睛和浓密的睫毛,一时难以入睡。我知道我不勇敢,但我想去看看。因为敬佩?因为好奇?因为挑战自己?因为想让更多人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人?都有。
2014年11月24日下午,穿过瓢泼大雨,我再次赶到城北某医院。
曹燕燕带我换上淡蓝色的医护服,戴上口罩和帽子,换上拖鞋,全副武装后,穿过“迷宫”——一个个挨在一起的手术室像一座城。我站在了欧阳的手术室前,隔着一块一本杂志那么大的玻璃窗。
一共十来个医生,包括从别的医院过来监督的权威专家、来接收器官的医生。
五个男医生全副武装在手术室门口待命,他们是来采摘器官的医生。他们每人抱着一个手术袋,只能看到帽子口罩或眼镜后面的眉眼,只听得见他们几句闲聊,声音很年轻。
“真伟大,能救好几个人。”一个声音从口罩后传出。
“医生救人是对抗上帝啊。唉,咱只好其他地方多积德了。即使对抗上帝也要做。”另一个声音从另一个口罩后传出,他手里缠绕着一根缝合线,反复练习着一个打结手势。
然后,大门关上,手术开始。我瞬间觉得空气是凝固的,呼吸起来要用点力。
欧阳安详地躺在手术台上,呼吸机已经脱掉,生命体征仪的波段,静静闪烁。医生们全部静立在前,等待他的心跳慢慢停止,曹燕燕和另一个负责见证记录的女协调员,正用摄像机拍摄记录现场。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否是我的幻觉,我看见欧阳的右手慢慢抬起来再慢慢放下,像在向这个世界、向他的亲人挥手告别。我的头皮发麻,心咚咚咚狂跳不止。
4点26分,欧阳心跳停止。
那一瞬间,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正坐在一张圆凳子上平复心绪,忽然感觉一阵风起,我身边五位医生像是突然听到了什么指令,全部刷地站起来,斜着身子冲进了突然洞开的手术室。
这时,我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哭声。是我的幻觉吗?
一位五十多岁的护工,正将我身边刚才医生们坐的一张张圆凳子搬到另一间空手术室里。我问他:“医生,怎么有婴儿的哭声?”
他抬眼看了看我,他大概有点困惑我的身份,但他大概把我当成协调员中的一位了。他口气平淡地说:“剖腹产也在旁边做的。”
他说“也”。在他眼里,一定生也平常,死也平常。
我呆立在手术室外的墙边,在无边的寂静中,听到了生死轮回巨大的轰鸣声。
(摘选自《守梦人》;苏沧桑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9月版)